黄帝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资源
陕西黄陵县的黄帝陵,是中华民族始祖黄帝的陵寝,有“华夏第一陵”之称。黄帝陵是中华民族圣地,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符号。
2015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指出,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轩辕黄帝陵文化积淀十分深厚,对历史文化要注重发掘和利用,溯到源,找到根,寻到魂。我们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深入挖掘历史文化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治国智慧,做到以文化人,以史资政。黄帝陵积淀的深厚文化内涵,正是新时期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资源。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也是中华文明的人文初祖。经过五千多年传承弘扬,更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华夏儿女团结奋斗的精神旗帜。悠悠五千年,黄帝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符号,黄帝陵则成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
一、中华始祖
黄帝本是部落首领,阪泉之战、涿鹿之战后,被尊为天下共主。黄帝、炎帝、蚩尤部族融合,构成华夏民族的基础。黄帝文化则发展成为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黄帝被确认为中华始祖,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先是口头传说,后是古史描述。黄帝开始只是华夏始祖,后来则变成华夏和其他许多民族的共同始祖。这以中华各族交往交流交融为基础,从原始社会,到魏晋南北朝,经数千年积累才完成。记录这一历史过程的代表性著作有司马迁《史记》,唐房玄龄《晋书》、李延寿《北史》、北齐魏收《魏书》等。
司马迁《史记》以《五帝本纪》开篇,而黄帝居首。他描述,黄帝是少典氏的后代,少而聪明,长大后修德振兵,成为天下共主。黄帝娶嫘祖为妻,生25个儿子。五帝中的颛顼、帝喾、尧、舜都是黄帝的后代。大禹所传的夏人,契的后裔商人,后稷的子孙周人,以及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多属黄帝血脉。司马迁系统记录了黄帝的血脉传承,确立了黄帝的华夏始祖地位。
司马迁还记载,秦人、汉朝人,都是黄帝的后裔。闽越人是越王勾践的后代,而越王勾践则是周太伯之后,与周文王一家。朝鲜王满本为燕人,是周召公的后裔,也和周人一家。西汉时期北方匈奴的先祖则是“夏后氏之苗裔”(《史记》卷110《匈奴列传》)。夏后氏,与大禹同姓姒,即夏人的后代。匈奴也属于黄帝血脉。南方“蛮夷”的先祖盘瓠,则是高辛氏帝喾的大臣,因有功,帝喾“以女配盘瓠”,并生子12人,6男6女,后来发展为族群,“号曰蛮夷”(《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广布中国南方的蛮夷也有黄帝的血脉基因。司马迁等汉代史学家已经构建起古史文化系统,说明中华大地多个民族都有黄帝的血脉基因。
从考古发掘看,中华民族始祖,前有元谋猿人、蓝田猿人等,从文献记载看,则有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等。司马迁等却认同黄帝是中华民族始祖,可以视之为汉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萌发的产物。
华夏文化经典《诗经》《尚书》不提黄帝,反映先秦大儒孔孟荀思想的《论语》《孟子》《荀子》也不言黄帝。《国语•晋语四》记载,炎帝、黄帝是兄弟,为少典氏娶有蟜氏所生;黄帝姓姬,炎帝姓姜。有关黄帝的文献记载流传很少,更多的只是传说,而且“其言不雅驯”。司马迁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西抵崆峒,北达涿鹿,东至于海,南到今江浙、湖南、云南。所见各地风俗不同,但多言黄帝遗迹。他才断然将《黄帝本纪》作为篇首。
战国中期,黄老学派开始尊崇黄帝。汉初,朝廷崇尚黄老,无为而治,发展生产,尤其是汉文帝,厉行节约,轻徭薄赋,三十税一,国家很快富起来,成就“文景之治”。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推崇“道德家”,即黄老道家。司马迁尊崇黄帝,有黄老的家学渊源,也有黄老思想指导国家政策实践效果的检验。黄帝被确认为华夏和其他民族的始祖,适应了汉代维护和巩固多民族统一大国的需要。黄老学主张无为而治,在实践中被理解为君主无为,臣下有为,受到诸侯国支持。汉景帝时尾大不掉,导致七国之乱。汉武帝即位,继续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诸侯国势力。在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只能在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上采取措施,维护和巩固多民族大国的统一。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地方推广郡县制。思想文化上,表彰六经、罢黜百家,催生两汉经学,为国家提供意识形态支持,又创立三纲五常为帝国提供道德规范约束。黄帝始祖地位的奠定和认同,适应了这一历史需要。
以司马迁为代表的汉代人已经认同黄帝是民族始祖。这种始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表现。随着华夏汉族和其他民族愈益密切的交往交流,这种始祖认同也得以发展,民族认同意识日益增强。黄帝成为中华各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粘合剂。
魏晋南北朝时,国家分裂,黄帝意识勃发。房玄龄等编撰《晋书》,记载北方民族史,多以黄帝为始祖,洋溢着中华各族天下一家的意识。当时,民间有人在鄠县自称“大黄帝”(《晋书》卷106《载记第六》),聚众数千,建元龙兴。建立大夏政权的匈奴人赫连勃勃,熟悉黄帝事迹。以黄帝、大禹血脉后裔自居,“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国称大夏”(《晋书》卷130《载记第三十》)。他说:“昔轩辕氏亦迁居无常二十余年,岂独我乎!”以黄帝为据,力主以游牧骑兵对付后秦姚兴,说:“吾以云骑风驰,出其不意,救前则击其后,救后则击其前,使彼疲于奔命,我则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岭北、河东尽我有也。待姚兴死后,徐取长安。”其口头禅是“朕大禹之后,世居幽朔”,今“将应运而兴,复大禹之业”(《晋书》卷130《载记第三十》),有意识地凸显其黄帝-大禹血统,强化其政权的正统合法性。
两晋南北朝时,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他们针对“自古以来诚无戎人而为帝王者”(《晋书》卷104《载记第四》),“自古以来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晋书》卷116《载记第十六》)等意识,要打破宿命,开辟非华夏族中原建国的历史新篇章。为此采取了三方面的措施:
一是认同黄帝始祖,强化民族基因中炎黄血脉的正统性。前燕奠基人慕容廆,昌黎棘城鲜卑人,“其先有熊氏之苗裔”(《晋书》卷108《载记第八》)。有熊氏即黄帝。前燕演变出的后燕、南燕、北燕等鲜卑慕容氏政权,皆属黄帝后裔。前秦氐族苻氏,“略阳临渭氐人也。其先盖有扈之苗裔”(《晋书》卷112《载记第十二》)。有扈,即有扈氏,与大禹同族。略阳氐族,也是黄帝的后代。后秦羌族姚氏,“其先有虞氏之苗裔”(《晋书》卷116《载记第十六》)。有虞氏即舜。北魏鲜卑拓跋氏,自称祖先“出自黄帝轩辕氏”,追根溯源到黄帝。因为“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北史》卷一《魏本纪》),完全以黄帝后代自居。
建立后凉的吕光,也是略阳氐族。他“追尊吕望为始祖”(《晋书》卷122《载记第二十二》),认为西周太公吕望是自己的始祖,自认“炎帝之裔”。北周宇文氏,自称“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周书》卷一《帝纪第一·文帝上》)。他们都自称属炎黄血脉,居华夏正统。
可见,认同黄帝、炎帝等是自己的民族先祖,在当时少数民族政权中比较普遍。以为血缘正宗,便政权合法,反映了西周以来嫡长子继承制的宗法政治意识。
二是认同中原是华夏中心,千方百计兵进中原,在此建国。如前赵占领关中平原,后赵扩及中原、河北、山西等地。时人以为后赵占据长安、洛阳二都及中原、北方,就可以“为中国帝王”(《晋书》卷105《载记第五》),成为正统;同时并存的南方东晋自然被视为分裂政权了。南北朝时,南方斥北方为索虏,北方贬南方为岛夷,南北政权都自居正统。这种政治正统意识,正是朴素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曲折表现。
三是在治国理政中学习应用黄帝以来的中原汉族文化,如汉语言文字、儒学等。建立北魏的拓跋珪意识到“《春秋》之义,大一统之美”,做帝王应“继圣载德,天人合会”,认识到华夏治国传统是“上古之治,尚德下名,有任而无爵,易治而事序”,秉持的治国原则是“道义,治之本;名爵,治之末”,而又“能通其变,不失其正”(《魏书》卷二《帝纪第二·太祖纪》)。北魏世祖拓跋焘率军攻灭大夏、北凉、北燕,统一北方,制定政策,推动鲜卑族的汉化。如进行文字改革和规范工作,奠定了魏碑基础。他下诏说:“在昔帝轩,创制造物,乃命仓颉因鸟兽之迹以立文字。自兹以降,随时改作,故篆隶草楷,并行于世。然经历久远,传习多失其真,故令文体错谬,会义不惬,非所以示轨则于来世也。孔子曰,名不正则事不成,此之谓矣。今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颁下远近,永为楷式。”(《魏书》卷四上《帝纪第四·世祖纪上》)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则整理孔庙祭礼,要求“尊明神,敬圣道”。下诏向全民求谏,要求“百辟卿士,工商吏民,各上便宜。利民益治,损化伤政,直言极谏,勿有所隐……使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北魏治国者有与官吏“共治天下”的意识,祭祀舜、禹、周公、孔子等圣人,重用汉族士子,建立基层邻、里、党三长制。要求官员们奖励生产,“劝课农桑,兴富民之本”,轻徭薄赋,“简以徭役,先之劝奖,相其水陆,务尽地利,使农夫外布,桑妇内勤。”(《魏书》卷七上《帝纪第七·高祖纪上》)。实行均田制,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全面推动汉化,迁都洛阳,以汉服代替鲜卑服,以汉语代替鲜卑语,下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下诏改鲜卑拓跋氏姓元。治国理想是“胡越之人亦可亲如兄弟”(《魏书》卷七下《帝纪第七·高祖纪下》),此言正是后来唐太宗华夷一家说的张本。
魏晋南北朝时各民族政权,血缘上认同炎黄始祖,文化上努力汉化,以中华正统自居,有力推进了中华各族的融合,为大唐盛世来临准备了历史条件。黄帝始祖意识在其中发挥了十分突出的作用。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鄜坊节度使臧希让奏称:“坊州有轩辕黄帝陵阙,请置庙,四时享祭,列于祀典”,得到朝廷批准。黄帝陵在唐代宗时正式出现于史籍记载,可以视为中华各族融合成果的符号化表现,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的表征。
图片
二、华夏旗帜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也是中华文明的人文初祖,经过几千年传承弘扬,更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团结华夏儿女的精神旗帜。黄帝陵是高擎华夏旗帜的民族圣地。
据文献记载,黄帝时代,中华文明取得了奠基性成就。物质文明上,驯养和使用牛马,发明车、船,学会打井、养蚕缫丝,战争中使用铜制兵器。制度文明上,制作冠冕、衣裳,政治上,举风后、力牧等六人为相,设官治民,并设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国语•鲁语上》说“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给事物、社会各等级命名,让民众分别共享财产。精神文明上,发明文字,制定历法和甲子,美术、音乐、舞蹈都有发展。从考古发掘看,今陕西、甘肃、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安徽等地,都发现了大量仰韶文化中期(前6500年-4000年)遗址。当时出现了农业、制陶、纺织、冶铜等生产方式,诞生了文字、历法、音乐、舞蹈、宗教等文化,社会组织从氏族、胞族、部落,发展到了部落联盟,出现了中心聚落——早期城邑。如西安半坡遗址,在7000年前到6000年前之间,西安高陵杨官寨村也发现了6000年前到5500年前期间的文化遗址,两者地理相近,前后相续。可见,黄帝时期是中华文明大创造时期,发明了农业、制陶、冶炼、日历、舟车、屋宇、水井、弓箭、文字、医药、音乐、舞蹈等,还创造礼制,设官治民,建立了国家雏形。从此,中华民族摆脱蒙昧、野蛮,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黄帝当之无愧是中华文明的人文初祖。
黄帝文化不断发展,演变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性符号,成为凝聚、团结中华各族的重要精神纽带。这主要表现在历代黄帝祭祀上。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死,葬桥山”,指的就是今陕西黄陵县的桥山。司马迁《史记•孝武本纪》和《封禅书》均载,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拉开了帝王亲临黄陵桥山祭祀黄帝的历史序幕。中华儿女在桥山黄陵祭祀黄帝,从此成为中华民族的祭祖文化传统。
其实,祭祀黄帝的历史源远流长。5000年前,黄帝去世,第一次朝廷公祭黄帝。由黄帝的大臣左彻“削木为黄帝之像,帅诸侯朝奉之”(《竹书纪年》)。4000年前,舜时,祭祀黄帝成为制度。《国语•鲁语上》:“有虞氏褅黄帝而祖颛顼”“夏后氏褅黄帝而祖颛顼”,有虞氏指舜,夏后氏指禹,祭祀黄帝是他们的制度。近3000年前,周穆王是首位主持祭祀黄帝的天子。《穆天子传》卷二载,周穆王“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丰隆之葬,以诏后世。”距今2400多年,即周威烈王四年(前422年),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首次建庙专祭黄帝。2000多年前,汉武帝首次以天子身份,在今陕西黄陵主持黄帝公祭。这为后来在黄陵进行黄帝祭祀,即黄陵公祭,开了先例。距今1200多年,即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黄帝陵、庙出现于文献记载。从此,朝廷设官管理黄帝陵、庙,遣官按时祭祀黄帝,成为制度。
汉武帝公祭黄帝,适应了汉代多民族统一大国建设的时代需要,标志着黄帝祭祀的成熟。汉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阶段,华夏族和其他许多民族交融,形成汉族。祭祖活动也相应得以发展。汉族一家一姓祭祖,发展成为中华各族共祭黄帝,适应了汉代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以孝治天下”的国策需要。汉朝人从祭祖礼仪中提炼出忠孝道德,凝结为忠孝信仰,发展出经学思维,构建起三纲五常制度,黄帝祭祀都发挥了作用。
近代中国遭受列强侵略,黄帝意识成为团结华夏儿女振兴中华的强大精神力量。辛亥革命高举黄帝旗帜。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第一期,开篇四幅图画,第一幅即黄帝,称为“世界第一之民族主义大伟人黄帝(中华民族开国之始祖)”。孙中山1912年1月1日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3月派遣15人代表团赴黄陵祭奠黄帝,亲撰《黄帝赞》祭文:“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创造指南车,平定蚩尤乱。世界文明,唯有我先。”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共祭黄帝陵,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作《祭黄帝陵文》,明确定位黄帝“赫赫始祖,吾华肇造”。
黄帝祭祀历史悠久,内容丰富。今天我们祭祀黄帝陵,体现了后人对黄帝陵寝的尊重、对黄陵祭祀传统的尊重,更是华夏儿女向民族始祖黄帝的致敬!我们祭祀黄帝,感恩、缅怀奠基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杰出先祖,让无数炎黄子孙贯通五千年血脉,如兄弟,如手足,同气连枝,荣辱与共!炎黄子孙以黄帝文化基因为源泉、为纽带,凝聚共识,达成默契,就可以形成牢不可破、坚不可摧的中华文化共同体,促进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使占世界人口1/5以上的炎黄子孙,团结起来,同心同德,用勤劳智慧的双手,推动中华文明持续繁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三、精神标识
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还因为伴随中华各族的交往交流交融,黄帝文化成为中华文明的内核,黄帝意识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西汉初年,黄帝被尊为民族始祖,魏晋南北朝时,黄帝成为匈奴、鲜卑等学习汉文化的核心内容;北宋时,黄帝升格进入儒家道统,完全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符号。
在我国古代,民族意识和文明观相关联。儒学创始人孔子的民族观影响尤为深远。其要点有:第一,断定和肯定华夏、夷狄有相同的人性,遵循相同的道德规范、礼乐制度,遵循忠信、笃敬等道德规范和礼乐制度;第二,认为诸夏、夷狄都创造了文明成果,各自的文明程度和地位并非恒久不变。若诸夏“礼失”战乱,夷狄或更为文明。第三,孔子断定,有人性修养的人,可以改变社会落后面貌,发展人类文明。第四,孔子肯定管仲保卫诸夏文明的历史功劳。孔子民族观中,始终贯穿文明观念,他将民众利益和文明程度作为道德评价的重要标准。在孔子看来,一个人道德与否,不能局限于个人之间的信义。让民众享受实实在在的利益,保卫文明,避免野蛮化,才是衡量道德与否的重要指标。孔子为后人提供了道德评价的文明史标尺,影响深远。
以文野之分,定华夷之辨,是孔子民族观的要旨。不是看血缘种族的区别,而是看文明和野蛮的分野。黄帝是中华始祖的观念,超越了各族生物的、地域的狭隘界限,成为中华各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心理依据。依照黄帝始祖观念,匈奴、鲜卑等民族入主中原,或者华夏人散居夷狄,都没有民族心理障碍。正是在黄帝始祖观念下,华夏和夷狄才逐步融合产生了汉族,汉族又和其他民族融合,逐步形成了中华民族。其中,民族融合是表象,文明化发展才是实质。在黄帝始祖观念影响下,文明化成为中华各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主旋律。
在古人看来,文明的核心内容就是道德,而黄帝则是中华民族史上第一位“修德”者。司马迁《史记》以黄帝为篇首,开始凸显黄帝“修德”的意义。他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在他看来,“黄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泽深后世,故其子孙皆复立为天子,是天之报有德也。”(《史记》卷13《三代世表》)黄帝有哪些“明德”?黄帝站在中华大地,创造人类文明,带领华夏先民走出野蛮时代,跨入文明社会门槛,造福当时民众,福荫子孙后代。据司马迁《黄帝本纪》描述,黄帝的道德和事业统一,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带领民众发展生产(发展农业,发明劳动工具,掌握、积累天文历法等农学知识),改进民生(生活用具),造福民众;第二,开展军事行动,除暴安良,救民水火,保卫和平,维护公平;第三,足迹遍中原,建立统一国家,创建国家制度,设官管理,维护社会稳定;第四,创造文字、音乐、舞蹈等,发展文化,奠定中华文明基础;第五,一生“未尝宁居”,勤政爱民,成为后来治国者的榜样;第六,黄帝的子孙繁衍为中华民族,黄帝创造的文明发展为中华文明,黄帝本人也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福佑中华民族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民族共同体,福佑中华文明成为没有中断自然发展进程的人类文明。
在中华各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明史中,黄帝和德治是两个核心内容。
如前秦苻坚熟读《史记》,尊崇黄帝,赞叹“轩辕,大圣也,其仁若天,其智若神,犹随不顺者从而征之,居无常所,以兵为卫,故能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率从。”(《晋书》卷114《载记第十四》)他掌权后,大力推崇儒家文化,开庠序,弘儒教,“广修学官,召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孙并遣受业。其有学为通儒、才堪干事、清修廉直、孝悌力田者,皆旌表之。”(《晋书》卷113《载记第十三》)他还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优劣。
又如前燕奠基人慕容廆,西晋惠帝元康间,认为大棘城是“帝颛顼之墟”,乃移居于此,“教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地方战乱,慕容廆起兵“勤王”,“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乃建辽东、冀阳、成周、营丘、唐国诸郡,举用贤才,封辽东郡公。慕容廆尝言:“狱者,人命之所悬也,不可以不慎。贤人君子,国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穑者,国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乱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晋书》卷108《载记第八》)并著《家令》数千言以申其旨,坚信慕容氏“积福累仁,子孙当有中原”(《晋书》卷110《载记第十》)。当时一些中原士族介怀华、夷族别,不愿为慕容鲜卑政权服务,慕容廆苦口婆心加以劝说,谓“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东夷,但问志略何如耳,岂以殊俗不可降心乎”(《晋书》卷108《载记第八》)。这完全不以出身民族,而以志向、理想论人,和孔子文明的民族观相通。
宋代学者进而将黄帝描述为制订礼仪、实行德治的领袖。司马光《稽古录》言:“黄帝以民生有欲,衣食虽备,苟无礼义,则强凌弱,众暴寡,智欺愚,勇苦怯,于是始制轩冕,垂衣裳,贵有常尊,贱有等威,使上下有序,各安其分而天下大治。”南宋罗泌《路史》明言黄帝“先之德正,而后之以威刑”。在宋人眼里,黄帝完全成为儒家的德治或仁政天子、德主刑辅的治国君主了。
宋代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建设的重要历史环节。北宋时,黄帝不仅被视为儒家德治典型,而且升格进入儒家道统,这是黄帝完全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符号的历史标志。
“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孙复提出,孔子发现的“夫子之道”早有渊源,它“基于伏羲,渐于神农,著于黄帝、尧、舜,章于禹、汤、文、武、周公”。黄帝开始被纳入儒家道统序列。《论语·宪问》载:孔子说“作者七人”,究竟有哪七人,后人难定。著名理学家、关学领袖张载断定:“‘作者七人’: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张载认为,所谓“作”,指“上世未有作而作之者也”,“黄帝始正名百物”,将黄帝纳入他所构建的古代圣王传授道统。张载《西铭》还提出“乾称父,坤称母”说,从祭祀家族祖先、祭祀中华民族始祖中抽象凝练出尊崇整个世界的乾坤大父母,期盼人们抱有“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天下一家情怀。这意味着在正统理学家头脑中,黄帝被纳入世界结构和中华文明史道统中,超越了民族始祖的血缘意义,一跃而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和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
黄帝陵作为中华民族圣地,令人敬仰、感恩,我们在这里流连忘返,瞻仰、反省,可以振奋兴起,感受中华儿女血脉相连的亲情,兴起海内外中华儿女亲如一家的感受。国家“十三五”规划,拟以黄帝陵为中心,建设黄帝陵国家文化公园。2017年10月14日,成立了中共陕西省委黄帝陵文化园区工作委员会、陕西省黄帝陵文化园区管理委员会。黄帝陵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完成后,会给我们提供更好的平台祭祖、感恩、尽孝,让我们远方归来的游子感受始祖恩德,体验故园亲情,激发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中华仁爱情怀。
* 声明:此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有来源错误或者侵犯您的合法权益,您可通过邮箱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及时进行处理。邮箱地址:huangdiling2024@163.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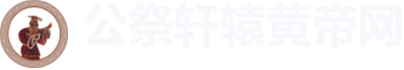
 无障碍阅读
无障碍阅读 长者模式
长者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