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祭祀活动要尊重历史
改革开放以来,各地都在大张旗鼓的举办各种始祖祭祀活动,在互联网上一搜索,《中国公祭》项目下,陕西黄陵的《黄帝陵祭典》、河南新郑的《黄帝故里中华始祖祭拜大典》、湖南炎陵的《祭祀炎帝陵大典》、甘肃天水与河南淮阳的《太昊伏羲祭典》、河北涉县的《女娲祭典》、浙江绍兴的《大禹祭典》都在其中。甚至有人提出要把新郑的黄帝故里上升到国家级大典,这也不无道理,因为我国历史上就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记载。虽然历史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对这种在新形势下出现的寻根问祖,祭拜我们共同的祖先的文化现象无可厚非。然而,由于传说与历史的区别,历史传说与考古学文化的挂钩,以及祭典与政治的原因等等,祭典文化中的乱象令人担忧。
一是不顾历史记载,站在地方立场上争故里。黄帝本是一个上古时期的传说人物,并且对黄帝的出生地有多种记载与传说。最有影响的一是渭水上游的陕甘交界或是宝鸡说,二是河南新郑说,三是山东曲阜寿丘说。最早提出黄帝生于寿丘的是《古文尚书》,唐以后,把《古文尚书》与《今文尚书》混为一谈,明清以来就已弄清《古文尚书》是伪造的,显然这个史料是不可靠,战国以前的先秦古籍中从来没有提到黄帝与曲阜有什么联系。新郑说的主要依据是有熊国。史料记载黄帝的父亲少典是有熊部落首领,而有熊国就在新郑,所以黄帝当生于新郑轩辕之丘。这个记载最早源于西汉焦延寿撰的《焦氏易林》。后来又有西晋的皇甫谧也说“有熊,今河南新郑也”。陕甘交界渭河中上游(宝鸡)说的依据是,《国语•晋语》:“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因姬水与姜水都在宝鸡,且这又是所有资料中时间最早的,与其它资料相比较,也是最具可靠性的。面对如此纷乱的史料记载,站在地方立场上,违背历史研究中史料引用的一般常识,不加筛选的一味强调有利于自己的某一记载,往往就得出牵强附会的结果,这是学术研究中不可取的。
二是牵强附会的把考古学文化与古史传说轻易挂钩。这并不是说考古学文化不能与炎黄文化挂钩,而是这种挂钩有没有公认的考古学根据,能不能取得共识。炎黄二帝都是中国远古历史上伟大的传说人物。因此在考古学文化中,为了处理好历史与传说,学者多把炎黄二帝作为远古时期的一个文化符号,这个文化基本对应的是仰韶文化的龙山阶段。但是要把这个阶段落实到一个比较具体的年代甚至某个具体人物身上,依据现在的考古手段是相当困难的,因此也就很难取得共识。目前最准确的也只能讲到创造这个文化的是那个部族。因此,离开这个前提,都说自己是故里,是无法取得共识的。
目前学界,特别是考古学界,基本的看法是,黄帝(部落)最早是生于陕甘交界的渭河中上游地区。理由是《国语•晋语》说黄帝因姬水而为姬姓是有根据的。陈连开先生认为,“陇山东西,泾渭流域是炎黄两大部落集团起源之区”。实际上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多数学者认为渭水上游的黄土峁原一带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这个文明后来是沿着渭水而下,到达黄河后沿豫晋交界向北、向东发展的。炎黄部落是处于中国史前文化这个大框架之内,一般来说就是指的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由于这个阶段没有文字记载,这就很难从考古学方面进行考证。依据《史记》五帝入,虽然多数观点把黄帝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进行联系,但也很难取得共识的。
从早期阶段来看,有几处遗址与炎黄文化的初级阶段有关,并且在相关地研究中经常提到。一个就是渭水上游地区的大地湾、宝鸡关桃园早期、北首岭下层,临潼零口、白家村等遗址。一个就是河南新郑的裴李岗遗址以及后来发现的具茨山岩画。这些遗存都处在前仰韶时期,与学界多数认可的黄帝年代相去甚远。最近发现的陕北石峁遗址,因其时代与黄帝活动的时间大体相当,由此有学者认为石峁古城“正是传说中黄帝部族居住的居邑。”为黄帝的都城,对此学界也是聚讼不休。陕西乾县出土的周成王时的《献侯鼎》铭文上的“天鼋”二字,学界多认为这就是文献中所说的黄帝的名号轩辕,说明从史前到商周时,轩辕或“天鼋”部族一直活动在渭水中上游地区。还有1978年甘肃庆阳发现的翼龙化石,翼龙就是天鼋,这也是黄帝部族为什么长期生活在渭水流域的一个证据。相比之下,渭水中上游地区的考古发现更支持《国语•晋语》说。尽管如此,对于黄帝及他所代表的部族到底生活在史前哪一个具体的时期,以及哪一个具体的地域,学界依然未有一致的认识。因此,在考古学上,硬要咬定某一地就是黄帝故里是片面的,起码从目前的考古学手段上是无法取得共识的。然而,把黄帝看作一个部族文化的代表和文化符号,就比较容易的解释炎黄文化研究中出现的故里说现象。因为创造这个文化的不仅仅是黄帝一代人,并且经历了数代甚至数十代数百年,这个文化也不仅仅是局限一个地方,并且有他的发展、迁徙与流向。这样,渭水中上游一带的宝鸡、陕北与中原地区的新郑,在不同时期,都曾是黄帝部族文化的中心。他们并不是相互否定的关系,而是源与流的关系。
三是要尊重历史现实,不要人为的另立炉灶,为了所谓的“国祭”,而否定自古以来人们就公认的黄帝陵的历史现实。中国历史上确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记载。但是,这个祭祀在各个时代的形式并不是统一的,也不存在什么“拜庙不拜陵”定式。《史记•封禅书》中说“秦灵公(前422年)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这是正史中对祭祀炎黄二帝的最早记述。那时,祭祀炎黄二帝的场所是“畤”,这个“畤”并不是什么庙,也不是什么陵。实际上,炎黄二帝本就是上古时期的传说人物,考古学上就不好确认黄帝陵葬的就是黄帝的问题。
然而,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华夏始祖”,却又是数千年来人们公认的传说历史。陕西黄陵县之桥山,是中华民族始祖黄帝轩辕氏的陵寝,是《史记》唯一记载的黄帝陵。不仅如此,黄帝陵东麓旁还建有黄帝庙,又名轩辕庙。据庙前碑文记载,黄帝庙始建于汉代,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朝廷重修和扩建轩辕庙,置黄帝庙于桥山西麓,宋太祖开宝五年(972)移建于桥山东麓,即今天的庙址。黄帝庙坐北面南,门前立一方形砖砌蚩壁,壁上书写着孙中山先生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的题照: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创造指南车,平定尤乱,世界文明,唯有我先。我不明白,面对这样一个华夏民族公认的事实,有人却提出“拜庙不拜陵”这个问题,也不明白为什么把黄帝陵与黄帝庙在这里要分开。因为陵寝庙宇本来就是帝王陵园上的建筑,早期是不好截然分开的,起码西汉时就是这样。《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述:“先帝园陵寝庙,羣臣莫习。”“拜庙不拜陵”的倡导者忽视黄帝陵起码从汉代就建有黄帝庙的情况下,提出“这就解决了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和陕西黄陵祭拜的关系”,显然是对黄帝陵上的黄帝庙视而不见。与其说“拜庙不拜陵”的倡导者是为了平衡各方关系,还不如说这是在混淆数千年中华民族的共识,制造新的混乱,撕裂中华民族对共祖的情感。
就新郑黄帝庙而言,除陕西黄帝陵上的轩辕庙之外,分布于中华大地上的黄帝庙数不胜数,这些祠庙都是炎黄子孙为了纪念中华人文初祖轩辕黄帝而修建的。这反映出炎黄子孙对于共同祖先的认同。这些轩辕黄帝庙宇,或存或废,或遗或圮,都是华夏儿女对黄帝这位人文初祖崇祀缅怀的历史见证。据不完全统计,全国黄帝庙就有四十多座。包括新郑西大隗山顶的轩辕庙和具茨山上的轩辕庙。前者的修缮时间为清康熙三十二年。后者虽说为明代以前所建,但也绝对早不到汉代。茨山上轩辕庙的门上方悬挂有原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题写的“人文初祖”匾额,门外立有前文化部部长贺敬之题写的“中华文明始祖”石碑一通。但与黄帝陵上的黄帝庙相比,无论是时代上还是参拜人的身份地位上,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一些在全国很有影响的专家甚至为了把新郑黄帝祭祀活动提升为“国祭”,竟然大言,新郑黄帝“大典已经做了十年,从各方面来讲。组织大典都具备了充分的经验”,殊不知黄帝死后,人们为了表达对这位人文初祖的怀念之情,就在桥山起冢为陵,立庙祭祀。在黄帝死后的几千年里,历代祭祀黄帝的活动从未中断。从虞、夏、商、周到秦、汉、隋、唐、宋、元、明、清,除了有的时段将黄帝同时作为“天神”、“帝王”祭祀外,都无一例外地将黄帝作为祖先祭祀。明代就将黄帝陵列为国家“祭典”。清代沿袭明代制度,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等皇帝先后派员赴桥山黄帝陵,进行祭祀活动。民国时期,每年清明节都要公祭黄帝。1937年清明节,国共两党派员共祭黄帝陵,毛泽东撰写的《祭黄帝陵文》,成为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出师表”,促成了国共的第三次合作与联合抗日的新局面,促进了全民抗日的胜利。改革开放后,大批海内外同胞到黄帝陵寻根祭祖,形成了清明节公祭、重阳节民祭的惯例。千百年来,黄帝陵一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寻根、铸魂、筑梦、聚心、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民族圣地。
因此,没有必要以所谓的“拜庙不拜陵”说,否定数千年以来华夏民族公认的黄帝陵公祭的历史现实,而人为的另立炉灶,搞一个新郑黄帝故里“国祭”。这样只能是给历史添乱,给学术添乱,给国家添乱,给民族情感添乱。没有任何正能量的积极意义。
(作者:刘明科 宝鸡炎帝与周秦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 声明:此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有来源错误或者侵犯您的合法权益,您可通过邮箱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及时进行处理。邮箱地址:huangdiling2024@163.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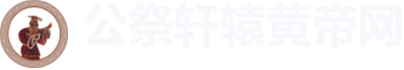
 无障碍阅读
无障碍阅读 长者模式
长者模式


